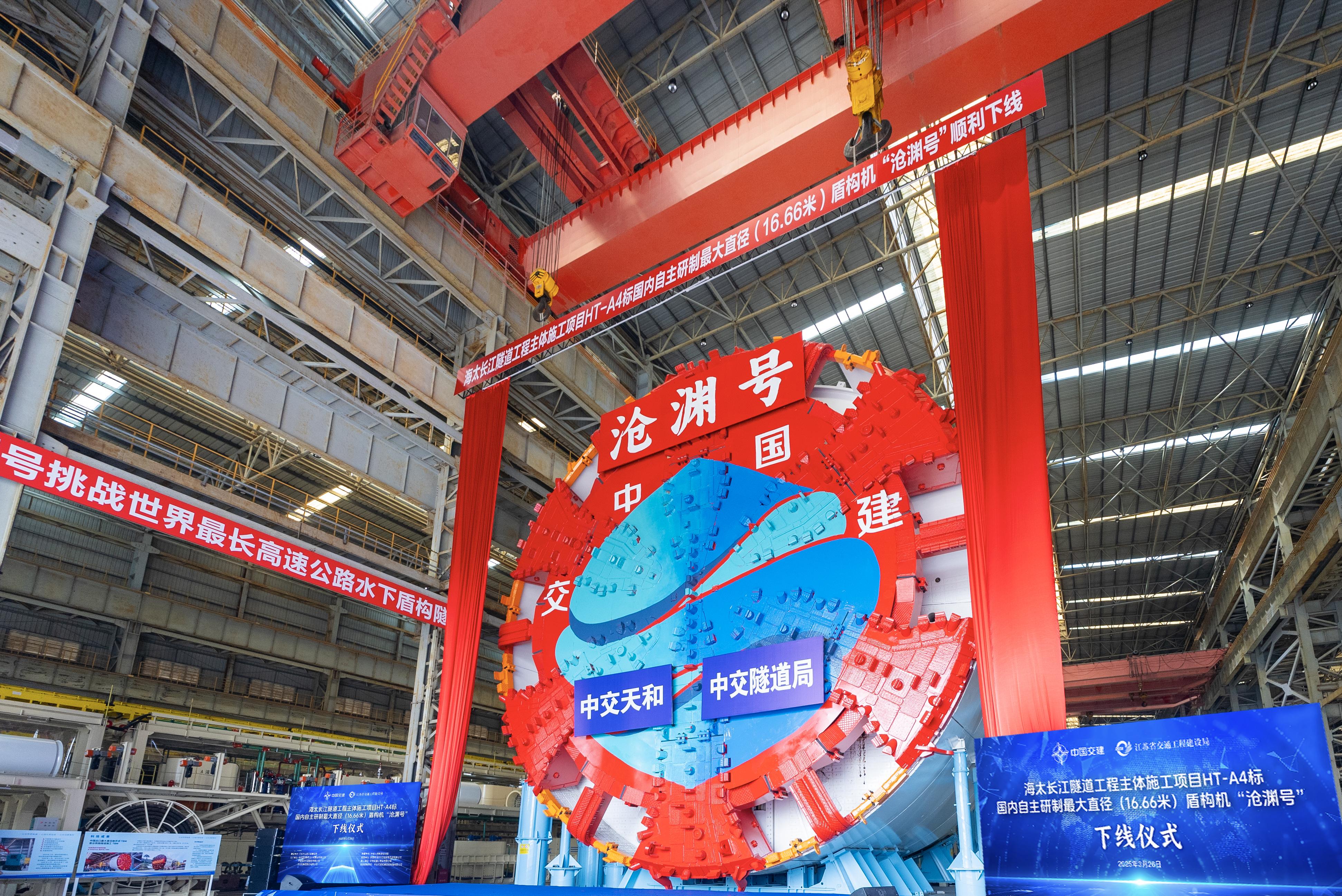是您撑起了那片天
“哒、哒……”一阵清脆的切菜声把我从睡梦中焕醒,天刚刚蒙蒙亮,母亲第一个起床在准备全家人的早餐,煮粥捞饭,热炒黄瓜片、炒花生米、赣菜萝卜干、韭菜炒鸡蛋四个小菜。一年四季365天,有364天母亲都是第一个起床,唯一一天是大年初一,父亲天不亮就起来放鞭炮接天地,热甜茶、五香鸡蛋准备早餐,母亲才能睡一个安稳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忙里忙外,有干不完的活。红白喜事要帮忙、人情世故要应付、大事小事要操劳、田间地头要管理、男男女女要关照,是您全力维持着全家的生计,是您为我们撑起了那片天。
长嫂为娘顾大局
在家族中我父亲兄妹五人,他是排行老大,祖母去世早,小叔和姑姑还未成家,母亲毅然承担起长嫂为娘的角色。
上世纪五十年末六十代初,自然灾害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父亲正值年轻力壮,每天上山挖许多葛根。母亲不辞辛劳地把成堆的葛根清洗捣碎过滤成葛根粉,大方接济给家族中兄弟姐妹们。记得二叔在旌德读高中的时候,一天返乡看见母亲挑着半担米糠回家。二叔对母亲说:“嫂子,我在学校饿得很,您看这米糠给我带点回去吧?”母亲二话没说,把半担米糠装进一个袋子里让二叔带到学校吃。从那以后每次二叔回家,母亲都给他准备一袋米糠,虽然全家正处于饥饿的边缘,但没有半点迟疑和不舍。
常言说:“牙齿都有打舌头的时候。”兄弟之间、邻里之间争争吵吵是常有的事,叔叔们同在一村又住隔壁,发生点纠纷矛盾,磕磕碰碰的事在所难免。记得有一次二婶在厨房里干活不知说了些什么话被隔壁大叔听到了,气愤的大叔赶到二叔家顺手就把炒菜锅给摔了,二婶也不甘示弱跑到大叔家把他家的炒菜锅抢了过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的不可开交。真是应证了“隔墙有耳”这句话。母亲正好走到二婶家找她看病,见此情景连忙把他们拉开,好心劝道:“兄弟家之间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非得大吵大闹,让别人家看笑话吗!”在双方冷静下来之后,了解事情原委,好言相劝做双方工作。母亲把二婶抢过来的锅还了回去,自己掏钱买了口锅给二婶家送过去。一场吵得天昏地暗的纠纷在母亲春风化雨般协调下两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叔家辛辛苦苦攒了点钱,想把老房子拆了重建。新建房屋在农村来说是一件大事,从开始用匠做饭、起屋请酒、预计人数、后厨管理,母亲前前后后协助三婶忙了半个月。花费前半生的积蓄盖起房子后,三叔家已是身无分文,举步维艰。正值年终,我家刚杀了年猪,母亲叫我一趟一趟给三叔家又是送猪肉又是送猪肠、猪血,尽其所能帮助三叔家度过年关。
母亲虽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识事明理,懂得关爱顾全大局,用她敞亮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把大家照顾的平衡有序,没落下一家,不亏待一人。
敢于抗争爱子女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我母亲对子女关爱有加,宁可自己受苦受累受冻也会把关心和温暖给予孩子。如果受到别人欺负一定会替子女出头,虽不会胡搅蛮缠,但定会把道理讲明白,把那口气扳回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外出养蜂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家中只有母亲和大哥两个劳动力挣工分养家。一次秋收之后生产队通知分粮食,大哥满心欢喜的挑着一担八斗箩去生产队等待称粮食。等了好半天终于轮到大哥,副队长胡维念对了一下工分薄,手按着八斗箩对大哥说道:“你家工分没挣够,这次没有得分。”口粮就是命根子,母子两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却分不到一粒粮食。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哥挑着空箩回到家,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母亲见状问他怎么回事?一开始大哥只是一个劲地哭,“到底怎么啦?!”在母亲一再追问下,他才说出了实情。母亲气呼呼地解下围裙一路小跑赶到生产队,找到队长,指着他就开始理论起来,质问他:“我们母子俩天天出工,有哪天偷懒啦?我家工分不够怎么就不能称粮食啊?他还是个孩子,就这么欺负人是吧?真是欺人太甚了!今天必须称一担粮食回家,不然饿死你维念负责!”掷地有声的话语把在场人员都震住了。等回过神来,维念忙向我母亲解释到:“顺,我完全没有欺负你家儿子的意思,是说你家工分不够这次不给你家分粮食,等到年底一起算有多少工分称多少口粮,不够部分再用钱来买。”“这几月我家喝西北风啊,有这么当队长吗?这次我就是要称一担粮食回家。”母亲针锋相对地说道。在相互僵持的时候,在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各家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刀切,灵活机动一点,你能忍心看着顺家的孩子饿肚子吗?”就这样,通过母亲奋力抗争和积极争取,分到一担粮食,也给大哥出了一口气。
记得三姐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胡老师一直没有给她发课本,天天上课没有课本,只能手抄听课。一天,母亲无意中发现三姐没有课本,就问她:“萍萍,人家都有课本,你怎么没有课本啊?”三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说:“老师说我家没有交学费不发课本,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发课本。”母亲沉默不语,表情凝重。晚上,母亲一个人提着煤油灯敲开班主任的家门,对胡老师说道:“晚上来打扰您们真是过意不去,但是为了孩子,找您商量件事。我家没交学费,不是不想交学费,实在是没钱,等她父亲寄钱回来马上就补交上。没有课本孩子怎么上课呢,就是大人有错也不能惩罚孩子啊?”第二天,班主任就把课本全部发到所有没交学费学生手中。
当风霜雪雨来临时,母亲就像一只雄鹰张开她那宽大而又温暖的翅膀把幼小雏鹰置于她的羽翼之下。用她那孱弱的身躯和坚强的斗志维护孩子的尊严,保护子女安全健康的成长。
晒向大地满春晖
母亲对子女的关爱恩泽就像雨露阳光,虽然是润物无声却处处感受到滋润和温暖。
1988年皖南山区久旱不雨,从7月初开始持续一个半月没有下过一滴雨,每天的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地里的庄稼一片青黄,稻田里也长出纵横交错的裂缝。正值水稻抽穗扬花时期,如果这时候缺水受旱那绝对是颗粒无收,一年辛辛苦苦劳作算是白干了。我家在平顶小山坡那坵田,面积有1.1亩种了水稻,因地势高东南北三面轮空,透风透气性好而且是沙土地很难存住水,满满的一田水过不了三天全干了。暑期里,我天天跟着母亲在横路里、八角灯等地方清理水道、寻查水路、引水抗旱、担水浇地。上有火球炙烤蒸发,下有拔塞放水灌溉,华茂塘蓄的水一天下降一圈,水位下降的非常明显,渐渐地池塘水位离出水口越来越远。水稻叶子被骄阳晒的卷了起来,田头东南角的水稻渐渐地发黄。心急如焚的母亲,经常自言自语:“日朝24个日头孔,雨毛都没有,那可怎么办?真是火烧张家店,早晚一场空喽。”
一天,母亲对我说:“武,你去问问庆红、林书他们的抽水机哪天有空?请他们帮我家抽水浇田,再不浇水全干完了。”望着焦虑万分的母亲,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好今天下午有空,抽水机在董家那片田间里,不过要自己去抬。”我找到他们之后对母亲说道。“抬就抬,赶快去,华茂塘里的水不多了”母亲说。我和母亲、三姐三人拿着棍子、绳索,沿着田间小道就朝董家走去。走了半个多小时,过了董家村约一公里的一处小山坳的池塘边找到了他们。“你们俩抬抽水机,我来扛水管。”母亲对我们说道。70—80米长,碗口粗的水管折成数节打捆,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的水管,从董家纹到华茂塘足足有3—4公里,一脚宽的田埂小路,弯弯曲曲一路上坡,真很难想像母亲当时是怎么扛上去的。抽完水,池塘见底了,我们是尽最大努力给平顶稻田灌溉最后一遍水,以后什么收成只好听天由命了。一个星期之后,苍天开眼下了一场透雨,不但拯救了地里的庄稼作物,也极大缓解了人们紧张焦虑的心情。真可谓:“天养人肥露露,人养人皮包骨。”作为出生在农民世家的我,亲身经历抗旱过的我,对“久旱逢甘霖”有一种切身的体会,那是喜极而泣而又刻骨铭心的感受。
记得我在绩溪中学上高中时,母亲已经把我当作一个正劳力来看待。家里有插秧、挑猪粪、割稻谷等农活一定会安排在周六、日来干。有几次秋收,周六一天没干完农活,周日一天接着干。那时周日晚上学校安排上晚自习,周一早上有早自习。从家乡到县城距离有39公里,用时近一个半小时,一天班车只有几趟。如赶不上周日下午最后一班客车,那必须起大早赶早班车回县城。从我家到上庄车站有2—3公里,途经五猖庙、风乎亭,沿途有许多坟地。深秋凌晨5:00点钟,天还是黑蒙蒙一片。虽经过一天的劳作,但母亲会准时起床叫醒我,然后陪着我一起安全走到汽车站,直到看着我坐上汽车座位上,“武,慢慢去哈。”母亲对我说道,而后朝我摆摆手才离开。我也摆摆手默默地看着母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苍茫的晨雾之中,才回过头来望着汽车前进的方向。母亲总是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交给孩子;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交给孩子。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我都能读懂她,那是对子女的担心、那是对子女的关爱、那更是对子女的期盼……
母亲是典型的徽州女人,在她身上能完全看到徽州女人的品质。母亲也是一位地地道道普通而又平凡的农民,经历过集体大食堂、三年自然灾害、集体化生产队、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十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次运动都留下母亲的足迹。只有深刻地读懂中国农民,才能更全面地读懂中国。
由于父亲多年在外养蜂奔波,在家的时间短,是母亲悉心照顾着我们,用她那并不厚实的肩膀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苦苦地给我们撑起了那片天。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相继送走了二姐、大哥和父亲,只剩归途的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今年重阳节格外思恋我亲爱的母亲,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依旧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可亲可敬,她的殷殷嘱托和声声教诲依然在我的耳边回荡!